两脚兽徒手教训美洲狮终合格斗最新比赛录像回放特尔施特根拒绝转交伤病报告
2025年7月,濮存昕艺术分享会现场,观众席坐满他的粉丝。上了点年纪的阿姨喊他男神,他不好意思地微笑示意。
大屏幕上闪过他在1990年代扮演过的一系列经典角色——高天(1996《英雄无悔》)、康伟业(1998《来来往往》)、贺援朝(2000《光荣之旅》)、田乔(1992《编辑部的故事》)、阿文(1993《我爱我家》),台下一片沸腾。
观众席里,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问他,“您坚持艺术创作这么多年的动力是什么?”
“因为我不会干别的!真的,不怕你们笑话。”他用诚恳、平实止息了观众席的声浪,“我16岁消了北京户口去黑龙江插队当知青,一去七年半,24岁返城回到北京,在考上空政话剧团之前,没着没落,档案上写着‘待业青年’,好多一起下乡的知青后来去了工厂、菜站,甚至很早都下岗了,我的才能并不比他们强,我能当上演员,后来还去了北京人艺,是想都不敢想的美差。”
这位7月底就年满72岁的“男神”没有刻意追求长得“不显老”,眼袋和法令纹自然呈现,任凭时光在脸上堆积雕刻,只有头发黑得不那么自然,是前几天为了给《南方人物周刊》拍摄封面图片而自己染的。
趁着“年轻”,7月中旬,话剧《海鸥》第二轮演出一结束,他便顶着一头乌发四处参加活动,走到哪里都能遇到当众向他表白的女性观众,阿姨们大多不年轻了,身边的先生一般也是他的影迷,不仅不嫉妒生气,还纷纷举着手机为太太与她们的“偶像”拍照拍视频,其乐融融。
与同龄人甚至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人站在一起合影时,濮存昕的形体显现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挺拔轻盈的身姿源自多年如一日的马术训练和瑜伽拉伸,饮食上也格外节制,“不敢胡吃海塞,明年还要演李白,体重大了,膝盖负担不了。”
他自言还能在舞台上蹦跶个三五年,尽管已经退休,演出仍然不停,6月主演了线月便以导演身份推出契诃夫的经典之作《海鸥》。短暂休整,8月底再回舞台中央,将在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经典线轮演出中担纲男主角罗切斯特。
从2003年开始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之后,濮存昕就很少参与影视剧的拍摄,但他在1990年代初塑造的一系列影视角色给他留下了延续至今的庞大的粉丝群体。
从最开始八个月拍一部电影,“挣四百块钱”,到后来一个月拍个烂片儿,“四万块,你干不干?”
“‘五斗米’赚到了,也有熟人观众批评我不该拍,但我想演艺这行当,首先当然是艺术,有时也为朋友、为挣钱。改革开放的真正动力是国人要富裕,过上好生活,我也是其中之一。”
他感念影视业给予自己的“第一桶金”,拍完《英雄无悔》,他和妻子一起去西单拿片酬,全是现金,“一大兜子,生怕遇上抢劫的。”
1995年,买了第一辆车,11万的二手日本皇冠,还是现金交易,去的时候盯着钱,回来的时候盯着方向盘,那是他头一次在北京路面上开车,“别跟我说话!”他冲兴奋不已的老婆孩子大声喊。
第一次在酒店住单人间也是拜影视业所赐。1991年,他主演话剧《李白》。一般来说,出去演出,为了保证主演的休息,会给安排一个单间,“但住单间,必须是国家一级演员才符合报销规定,我没学历,没论文,很长时间评不上一级。”
于是,“李白”在外地演出期间的睡眠质量只能靠运气,“头天同屋人打呼噜太响,第二天换个人,没想到,比昨天那个打得更响。”实在睡不着时,他大晚上跑到前台倒在门口的沙发上熬到天亮,“给蚊子咬的呀……”
1995年敲定了由他出演《英雄无悔》男主角高天,他在广州第一次享受到单间待遇,剧组的宠爱、优待、笑脸让一个新人受宠若惊。
在那个缺乏好内容、又有极大创作自由的年代,公安局长高天一边反贪破案,一边与三个恋人拉扯纠缠——1996年夏天,《英雄无悔》在全国热播,好评如潮,濮存昕就此扬名立万。
名利涌来的时候,拍摄中经历的痛苦和无奈如鲠在喉,当时的剧组没有劳动保护的概念,两个组同时开机,演员超负荷运转,制作选景很凑合。因为担心成片质量,他一度感到非常悲观,不知道这趟快车的终点会在哪里,“我有名利之心,担心自己辛苦半天,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最困难的时候,他读茨威格写的《伟大的悲剧》——《人类群星闪耀时》中一篇关于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的传记,获得了神奇的精神净化,“在失败面前,人格要站立。”
当时他只想着凭良心把自己的部分做好,“像那个船长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完全想不到这个快速扩充到60集的注水剧,送审播出的时候会被压缩成39集,恰到好处地解决了粗制滥造之嫌。
2005年,濮存昕从业以来职业幸福感最强的两部电影《一轮明月》和《鲁迅》完成,弘一法师和鲁迅这两个人物是影响他颇深的“生命样式”,他把这两部作品视为自己在人艺舞台上磨砺多年、作为一个成熟演员的“表演总结”。
没料到1996年踏上的那辆影视快车全速跑进了商业片时代,2005年,《无极》《神话》《头文字D》《哈利波特与火焰杯》横扫四方,《一轮明月》票房惨淡,“《鲁迅》压根儿就没有进入院线排片,零票房!”
自此他便淡出了年轻一代影视观众的视线,不进剧场的人,甚至会对这位昔日的明星脸盲。前两年有个短视频传得挺广,在上海静安寺附近,有位女士请身边的路人帮忙拍个照,“帮我把静安寺塔拍进来哈。”
“路人”不语,只是欣然接过她的手机,拍完,与“路人”随行的人提醒那位女士,“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濮存昕啊!”
《鲁迅》没有上院线,在作家、编剧黄宗江先生家,该片导演丁荫楠用电脑给黄宗江和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播放了这部片子。苏民是参与北京人艺创建的老一辈职业线年代开始就出演人艺版《雷雨》中的周萍,这个角色他一直演到五十多岁。“鲁迅”是苏民梦寐以求的角色之一,但没有在重要完整的艺术作品中扮演过,素来威严的父亲由衷感叹,“你真的很幸福啊,能够演鲁迅。”
拍《一轮明月》的时候,濮存昕的姐姐带着父亲和母亲前去探班,“我父亲连手都没跟我握,怕我从角色中跳出来了,又变成了他们的儿子。”
父亲望着儿子,用眼神肯定着他老年弘一法师的扮相——清瘦庄严,那是濮存昕每天临帖、只吃苏打饼干和一瓶酸奶得来的。
“濮存昕如果多拍电影,早该拿影帝了。他的表演有一种难得的文人气质,这是很多演员不具备的。”张艺谋导演不止一次地称赞濮存昕的演技,在拍摄《英雄》时,也曾与他联络接触,但因档期问题未能合作。
“林兆华导演说过你是真爱戏剧,为了排戏,放着外面挣钱的影视剧项目都不接。这十年不只是淡出,几乎是退出,这么做是想专注于舞台吗?”我问濮存昕。
他望着我,毫不犹豫地摇头,“这就是拔高我了。”习惯性的诚实让他笑起来淘气天真,“那会儿我已经担任人艺副院长了,院里当时有个提法,呼唤外出的凤凰们回来,栖息壮大咱们人艺的梧桐树,喊人家回来,你自己再跑出去,就太不合适了。”
在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中,他对读者也全然坦诚,“能在电视连续剧中演个半大主角,不长时间就能赚到买房子买汽车的钱。我们人艺舞台,观众席座位九百个,演一百场,场场都满座,一年下来也就九万个观众,一个中上等水平的电视剧,一晚上保守估计会有千百万个观众,能成为全国观众喜爱的演员,当然得在电视电影中露面,名利双收呀。”
他鼓励年轻一代的人艺演员出名,很高兴看到他们开着很不错的车去剧院排练、演出,“演员也要挣钱养家,当然有责任把自己、把家里建设好。”
“只是要记住咱们是演员,专业上咱得做到位。舞台是能创造奇迹的地方,演员在无所不能的舞台上创造生命能量的奇迹,这是观众买票走进剧院的理由。”
2020年,濮存昕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成为继田汉、曹禺、李默然、尚长荣之后,第五位中国剧协主席。当选致辞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演员,不停地在台上创作,与大家一样,是名舞台艺术工作者。我想表个态,买的时候什么样,卖的时候还是什么样。”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他特别强调自己是喜欢“专业主义”的,“只要专业精神树立起来了,歪七扭八的事就少多了,专业精神没有的话就会节外生枝,好多你意想不到的乱象就出来了。”
他笑言自己有几个“典型”噩梦,刚回城的时候,“经常会梦到知青返城撤销了,不让回城,必须重新回到北大荒。”当了演员之后,最大的噩梦是“在台上忘词”。
“想要在台上自信自如,排练的不同阶段,每步都不能掉队。”在专门分析剧本、参考资料的阶段,演员不用功,对词就会苍白。对词的时候再不用功,“到上场走调度了,你已经是顾得了吹笛顾不了捏眼了。”到连排的时候,演员如果仍然不能主动驾驭自己,无法让角色驱使自己,“到了舞台上不可能给予观众真实感。”
6月底的北京暑热难熬,下午3点,话剧《海鸥》第二轮演出的排练场,一阵风油精的冷冽冲散了昏沉。
他用下巴给我指了指导演位置上的濮存昕,我们相视一笑。话剧演员“触电”之后,仍然乐于回到排练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有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踏实感。我和摄影师两张生面孔很快就被接纳,演员们从身边走过时,都会用眼神或者微笑向我们释放善意。
5点半,四个多小时的连续排练终于结束,濮存昕招呼大家集合,“亲爱的们,咱们明天继续,明天还是1点开始。”
主演李越说,两年前第一轮演出时的排练很苦,“从排练到合成,真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关在剧场里,不知道外面是天黑还是天亮,空气也是凝固的,舞台上布满灰尘。”
契诃夫经典剧本中的台词非常容易抓住演员的心,剧中两个作家感受到的创作的孤独和写作压力“无尽的轮回”,让李越读出了心声。
今年32岁的李越饰演的是苦闷的年轻作家科斯佳,1991年,时年38岁的濮存昕也扮演了这个角色,当时剧院请来了前苏联著名导演叶甫列莫夫亲自执导,濮存昕为此放弃了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出演诸葛亮的大好机会,但他逢人就说,“我演得不好。”
转型做导演后,濮存昕选择的三部话剧《哈姆雷特》《雷雨》《海鸥》都是他1990年到1991年参与演出过的。
“我理解得对吗?这样处理对吗?”越是演得久,越会想得深,濮存昕总记着父亲的那句话,“似有乎悟,仍有所思。”
对于自己40岁之前参演的三个重要剧目,他渴望更深挖掘其中的奥义,“演员和导演是俩行当,各有山头,在一个个戏里,我和导演们各自攀爬自己的山头。”
他知道演员横跨过“山梁”,去爬导演的“山峰”,是有短板的,“会多从演员角度出手,而在文学和舞台设计、灯光、音响等方面有欠缺。”
2025年6月27日,濮存昕在话剧《海鸥》排练现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这是我的导演习作,请多提宝贵意见。”7月1日傍晚,《海鸥》第二轮正式演出的前一天,《南方人物周刊》受邀观摩彩排,濮存昕站在北京人艺曹禺剧场门口迎接各方的朋友们。
“契诃夫的戏不好排啊!”演出正式开始前,他轻轻走到观众席,在童道明先生的女儿童宁座位旁的台阶上坐着聊天。我扭过头拿着童宁的手机给他们拍合影,虽然他俩都已经退休,但两张面孔干净舒展,照片拍出来有种在大学阶梯教室的感觉。
于是之、蓝天野、童道明三位是提携和帮助过濮存昕的三位师长,童道明青年时代留学苏联,用从俄语版本直接翻译过来的契诃夫剧本丰富了焦菊隐先生的英译本,童宁在整理父亲遗稿的过程中也爱上了契诃夫,她通过校译、翻译与父亲童道明隔空接力,完成了最忠实于原作的契诃夫戏剧选《樱桃园》。
“新戏上演的时候,就是剧院的节日。”濮存昕一直呼吁人艺要排新戏、排重要的剧目,“一个剧院如果没有新戏就死了。”
“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海鸥》的意向性是最强的,他以情感流动替代事件驱动,淡化故事线,注重人物心理与日常细节,要演好,不能靠吼台词,甚至不能靠‘演’,演员需要具备相当的成熟度。”
言语温柔的童宁惜字如金,她对濮存昕执导的《雷雨》赞叹有加,点评《海鸥》时看得出来她的为难,“我父亲说契诃夫所写的人物都与自己的环境充满了冲突。契诃夫的作品里总有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提醒人们另有一种生活——干净纯正,有教养有秩序,这是契诃夫的戏剧中最重要的一种理想,而不只是那些困乏失意。所以《海鸥》的‘飞翔意象’不应该被消解,男女主角科斯佳和尼娜身上的理想主义气质也可以传达得更明确。”
首演结束后,濮存昕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说,彩排当晚,自己做了一个梦,“票房那边跟我说,‘有一千张工作票,你们可以免费送!’一千张工作票!说明票卖得一点也不好!”他吓醒了,一看表,才6点。
“排戏这么辛苦,年轻人都想躺平,您都退休多年、功德圆满了,为什么要在排练厅受罪呢?”
这个问题,我问过濮存昕两次,第一次是6月底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下午,排练结束后的他既轻松又疲倦,说话的时候,眼神常常放空,“不排戏,做什么呢?”
他的眼睛望向你的时候,非常安静,“戒定慧,到剧场来,也像是一种持戒吧,持定了这个,其他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下,都可以拒绝掉。这个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做这个就很好了。”
7月初在马场专访他的时候,我又问了这个问题,“就像那天,您跟童老师说的一样,契诃夫的戏不好排,基本上叫好的都很少。您年过七十,德高望重,名利双收,职业生涯很圆满,啥也不做保持着美好不也可以吗?”
“年过七十,德高望重,”他一边重复一边大笑起来,说自己就是很想“补课”,“我自己演的时候没做好,我想象可能能做好,这是我的动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希望能带一下剧院的年轻演员,“他们需要演一些重要的戏。”
跟濮存昕合作多年的龚丽君,在人艺版《雷雨》中演了三十多年繁漪,正所谓“铁打的《雷雨》,永远的繁漪”,濮存昕数度与她合作《雷雨》,随着年岁增长,从周萍演到周朴园。
为了繁漪这个角色,龚丽君二十多年没剪过短发,一直留长发,“戏比天大,你的一切都是戏的,是剧院的。票都卖出去了,你都不能随便生病,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角色,也就保护了剧院。”
2014年,两位老搭档开始合作演出《洋麻将》,这是一部场景设在养老院里的两个老人之间的戏,最开始,他们还要“扮老”,这两年发现真的老了,“于是之老师当年演这个戏时还没到六十岁。”
在一场演出中,濮存昕饰演的魏勒戴的老花眼镜腿儿断了,他试了几下不行,鼻梁上架不住,“当着观众,我从容地把眼镜揣进口袋接着演,可眼睛老花是真的,我瞪着桌布,看不清道具牌了……”
坐在对面的龚丽君笑而不语,用她丰富的舞台经验不动声色地“救场”,一场戏下来,“好家伙,大冬天,我出了一头的汗,快迷住眼睛了,直到中场休息,化妆组拿来备用花镜,才得了救。”
新冠疫情结束,北京人艺第一场对观众售票的戏正是《洋麻将》,今年6月,两位搭档再次联袂,“明年还要演十几场。”
《海鸥》第二轮演出结束的第二天下午,我和两个同事一起坐在鼓楼西小剧场的观众席上,和现场两百多人一起吼着《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的经典台词,在台上给我们做指挥的正是“导演”濮存昕,每当观众齐声喊出哈姆雷特的内心独白,坐在台词提示屏后面的他都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这是他的一堂表演公开课。
“好玩儿吗?”散场后他一边给买了他的自传的观众签名,一边问我,自己先乐开了花,“好玩吧!”
把哈姆雷特的台词分给其他角色演,是导演林兆华1990年初排实验话剧《哈姆雷特》时就玩过的高招儿,“天啊,这人物关系让人都糊涂了!”当时还是戏剧新人的濮存昕一头雾水,追着问林兆华,“你这是什么意思?人人都是哈姆雷特?人人都有这种心理困境?是这个意思吗?”
“你的戏没道理!”濮存昕的父亲一辈子从事戏剧演出和戏剧教育,当着林兆华的面,老先生坦诚以告。
濮存昕想听听父亲夸奖自己扮演的哈姆雷特,“没有。”但他从那时就知道,林兆华让舞台上的自己更真实,更自由了,“原来还可以这样演戏。”
多年之后,他自己做导演带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的学生排《哈姆雷特》时,仍然不敢用角色互换的方式。
这一次在小剧场做大师课,算是过了一把瘾,小剧场观众坐成U字形,从观众席一直延伸到舞台两侧,将三个事先稍有训练的男生包围在台上,他们三个轮流扮演哈姆雷特,老王的鬼魂、旁白还有雨夜的音效全由观众来承担。舞台后方立着一个电子显示屏用来提示台词,观众个个入戏飞快,感情饱满到过剩,把台词念得震耳欲聋。演员们看起来台词也不是很熟,“哈姆雷特”时常抱住显示屏,痛心疾首、陈明心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个“哈姆雷特”被“群众演员”的热情和投入感召,一轮比一轮卖力,无形中竟斗起戏来,技术不够情绪来补,一个小伙子演得汗湿上衣,观众被他在台上释放的生命能量感动到了,濮存昕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狠狠赞赏。
“我很感谢林兆华,他教我如何拆解自己,能够不停创造出新的形式、新的空间、新的表演,创作的本质是即兴。”
也许是两百多个观众又跺脚又呐喊,一朵雨云倏忽而至,散场不久,天边几声炸雷,众人催促濮存昕快点离开。
他走到门口,忽然被一位白发观众拉住了手。这位阿姨方才在演出中被一个演急了的“哈姆雷特”从观众席上拉到台中间随机搭戏,表现得十分沉稳自如。濮存昕见状激动地凑上来,结果老阿姨瞬间出戏,一直对着他耳语,表达粉丝见到偶像的激动。
“咱们是同龄人啊,您多保重身体,常来看戏。”濮存昕钻进车里,从车窗把手伸出来,举得老高,“再见啦!”
2025年7月12日,北京鼓楼西剧场,濮存昕在表演公开课后与观众合影(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我原来有个绰号叫‘快节奏’,那时候刚考上空政话剧团,从知青转变成一个演员,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太多东西着急要学习,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王贵导演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绰号。”
跟濮存昕面对面聊天是非常愉快的,就像大多数赛车手日常开车时仍然会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一样,话剧演员也会不自觉地控制自己的发声与共鸣,用舞台上千锤百炼过的声音展开闲谈。
2025年7月,话剧《海鸥》第二轮演出顺利完成首演后,导演濮存昕在家附近的马场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专访。他特地将采访地点安排在马场是因为每天上午在马背上专注舞步的这一堂课是他身心最放松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能想,一分心人就从马上掉下来了。”
他的马叫“知青”,快20岁,从欧洲买来的时候才7岁,如今已经是匹老马,马的寿命一般为25到30岁,“有人建议我再买一匹能出成绩的好马,不要,我训练也不是为了拿名次,就让我陪它终老吧。”
教练说一堂课一般是45分钟,“很多学员刚来的时候会说一节课才45分钟吗?上马不到20分钟就会哀求,教练啊……好累啊,时间差不多了吧……濮老师对自己要求高,基本都练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不到,濮存昕的白色训练服已经汗透了,马也累了,教练把“知青”牵到后面冲澡。濮存昕把提前准备好的胡萝卜拿出来奖励它,毛发油亮、肌肉紧实的“知青”吃东西的时候暴露了年龄。为了保护它的牙齿,濮存昕在家里特地给胡萝卜打上了花刀,方便心爱的老马啃咬。“‘知青’是能跳障碍的良马,为了我的安全,改练舞步了,它还能跑五年没问题,我如果保持好自己的状态,也还有五年能够在马场和舞台上蹦跶……”
72岁的濮存昕是这家马场年龄最大的学员。在黑龙江做知青时养过马,50出头开始接触专业的马术训练,濮存昕练过障碍赛,又转而练习盛装舞步,到现在也不是骑着玩玩,今年仍然会参加盛装舞步公开赛。
我们的对话在马场的咖啡厅进行。从训练场往咖啡厅走的这一路,他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点头微笑,一坐下就轻快地招呼着咖啡厅的小伙子,“我们都喝热拿铁,还有柠檬水,从我卡里扣哈。”
聊了一个半小时,他又张罗一起去旁边的餐厅“草料场”吃午饭,“吃我的,我是一个大款。”
这些瞬间让我充分理解了为什么他的身边人都爱叫他“小濮”、“濮哥”——尽管年过七十、成名已久,尽管被称为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还担任剧协主席,但他的性格底色一直是明亮、轻快、自如的“北京小哥”。
南方人物周刊:昨晚演出结束后,大家聊几句总结一下,你到家得夜里1点多了吧,今天9点又开始马术训练,累不累?
南方人物周刊:怎么能够调整得下来的?比如说现在不想排戏的事,马上就不想。
濮存昕:我们演员这个职业是这么一个节奏,现场导演喊着“开始”、“好”、“停”、“重新开始”。一声“重新开始”,演员马上就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
我们有长期演出,一个戏少的十来场,多的要连续演出二十来场,每天重复,加上现场演出的压力,人会很累,心理上必须有一个中间的调整。要训练自己有一个时间段完全放下,放下再想起,找到这个感觉。
其实今天也安排得很满的,上午接受你的采访,下午还有个接待,晚上剧院有演出。我现在跟你对话的时候,我就专注在谈话上,脑子里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想。高度集中,完了之后就进入下一个任务,转换得非常快,这里面也有一种态度,是一个好的训练——平等地面对当下。
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你第一次在北京人艺排《海鸥》,今年是第二轮演出,前几天我在排练场待了一个下午,感觉你是一个很宽容的导演。
濮存昕:(笑)表演毕竟是要由演员在台上完成的。我父亲他们那一代都喜欢说“导演要隐去”, 彼得·布鲁克的演员们也说过,“大师给我们排戏的时候,让我们把他扔在化妆间,不要带上台。”
表演最大的魅力是即兴,导演和演员通过台下的训练,把一些系统确定下来,类似于一种基本固定的玩法,但是一上台,应该把它都变成即兴的。话剧、影视都是还原生活的艺术,但我们在舞台上是在假定的前提下去还原真实,我们怎么把假定的东西变成特别具有真实感的东西,这种即兴状态是最拿观众的。
我们必须允许演员有他(她)个人的东西,没有个人的东西一定不行,但是个人的东西是和角色有关的那部分,和角色没关系的我们在排练时尽量地帮他们调整一下。导演给演员一个方向,让演员自己来找比例。
南方人物周刊:1991年,北京人艺请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过来排《海鸥》,为了参与这部戏,你放弃了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扮演诸葛亮的机会。这是你接触契诃夫戏剧的开始,后来你几乎把契诃夫所有的剧都演了,但总说自己演得不好,特别是《海鸥》,真的有那么不好吗?
濮存昕:是真的不好。那时候的我,说完自己的台词就完了,说台词也就是基于通常的想法和通常的情绪。
新冠疫情期间,剧院没有演出,在家待着没事,我就把剧本拿出来重读,剧本都发黄了,一读忽然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内容,人物之间的关系全串联起来了。当时就特别想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重新排一次《海鸥》。我当年没有演好,岁数过了没有合适的角色不能再演了,我尝试着将这个作为自己的导演习作拿出来给观众批评。
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你带着人艺的年轻演员们排了《海鸥》,演了第一轮,你觉得今年这次演出是不是更成熟、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了?
濮存昕:契诃夫的戏不好排,他的剧本小说化,人物内心中平静的澎湃、诗意的表达,以及台词的反转,处理好都不容易。
作为导演,也需要问自己,契诃夫是这样想的吗?我的理解,四维空间的契诃夫如果看了,会点头说,对,这个理解是对的吗?
我不敢说自己能做得多么好,第一轮演出的时候,我在家临帖,写的就是“半称心”,这出自于李叔同先生——“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作为一个导演“习作”,“半称心”就知足。
第二轮并不是直线往上进步的,这轮演出目前我的感受是半称心的半称心。当然观众也有表扬我们的,夸我们进步了,但是也肯定有不少批评。昨晚上我看演出,又有很多触发,好多台词可以处理得更好。我现在是控制演员们的情绪,他们见到观众,情不自禁想卖力气。
目前票卖得还行吧,票房说周末的时候会涨起来一点,我们现在很容易满足,只要在涨就很开心。票房很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院团,我们做的还不只是产品,更是文化事业,《海鸥》是国际上重要的院团都会排的剧目,院里也希望把它作为我们的保留剧目留下来,第二轮演出也还是刚刚开始。
南方人物周刊:契诃夫的戏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院团排得都非常多,据说仅少于莎士比亚,但似乎广受好评的都不多,即便俄罗斯导演排出来的也一样,国内林兆华导演排过、李六乙导演排过,你都参演了。
濮存昕:我以前感觉演契诃夫的戏特别痛苦,他写的角色好像都很失意,我也演得有一点消极沉闷。后来我看到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导演他们排的,比如契诃夫的《婚礼》等等,每一个人都极其自信而强烈地表达自己,直来直去,再过不去就决斗了,砰砰砰就干了……
我感觉自己的认识更新了,再后来又有机会去俄罗斯,真实地感受那片土地,这些都是无形的启发,演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慢慢离开自己了,或者是有自己又有那个角色了。
(停顿——如同契诃夫剧本里经常会出现的让现场导演和演员抓耳挠腮的两个字“停顿”)
南方人物周刊:戏剧导演不仅是演员和表演调度,更是把剧本的意义之光打到演员前面,让演员在舞台上达成一个艺术表达。作为导演,你特别有触动,想表达的是什么?
濮存昕:我自己对《海鸥》有一些理解,我还是比较自信的,我感觉契诃夫也许会在四维空间里看到我们的版本,称赞我,说我理解对了。
海鸥是一个意象,海鸥很美,但它其实是猛禽,欲望极强,它们不飞翔,因为美丽的湖水中有许多鱼虾。海鸥沉溺在其中,如同人们沉迷于世俗生活。
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都在为世俗利益争夺,无法高飞,舞台上那两棵枯树,是人与环境冲突的象征。
人类最大的智慧是利他,替别人着想,秩序就出现了,然后彼此之间关系的分寸就出现了,社会也会稳定,人们可以拥有契诃夫笔下的角色所期盼的一种光明的美好的生活。
但是现实是海鸥不飞翔,人也好、国家也好,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科斯佳开枪自杀的时候,那一声枪声里你仔细听其实还有很大的枪炮声,那是俄乌冲突、中东战火的枪炮声,我让音效师加进去的,是有点寓意在里面的。
这个意思其实契诃夫通过科斯佳写的那个剧本表达出来了——因为人的争斗,二十万年后地球上没人了,没有生命了,一切由造物之手重新再做安排。
南方人物周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你排这个戏的追求。不过坦白说,我自己没看到这个高度和深度,我很怀疑年轻的演员们是否能想到这里,我感觉大家更容易从个体感受出发,被戏里困在自己生活中、爱而不得、无法过上理想生活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物而触动。
濮存昕:演员可以沉浸在爱恨情仇中,但是他们要懂得契诃夫是怎么描写的,而不是单凭自己的理解。
我不能教他们怎么演,我只能要求他们在排练时少用“我觉得”,而要多读剧本,谈角色的时候,用“剧本里写”,通过这种约束让演员更快找到角色逻辑。
南方人物周刊:喜欢契诃夫的读者和观众非常多,各有各的理解,很多导演都因为排契诃夫的戏受到过批评,如果有人发表文艺评论批评你的这个版本,你会难过吗?
濮存昕:我们当然喜欢听表扬,但是如果别人批评我,我就像《海鸥》剧本里的作家特里果林说的那样,“如果有人批评我,我就难过两三天。”(笑)
(记者注:1991年版《海鸥》演出后,媒体反映冷淡。濮存昕在《我和我的角色》里幽默地写到,于是之老师还专门请媒体吃了高级西餐,但评论寥寥,“大餐白吃了。”)
林兆华导演把《等待戈多》和契诃夫的《三姐妹》组成了一个戏,我和陈建斌参与了演出,开研讨会,只有《北京文学》副主编李陀一个人说好,他写文章说那是林兆华导得最好的一部戏。
南方人物周刊:你为什么冒险要排《海鸥》,还带着这帮年轻孩子,你自己也知道这个戏演好需要很强的演员阵容。
濮存昕:自己当年演的时候没做好,没理解透,想补课是一方面,第二个是剧院里这些孩子,他们也需要参与演出重要的剧目,我们年龄大一点,不能不负责任,当然也可能承担得有点太多了,退休了还在承担,但我喜欢那些专注、努力、负责任的年轻演员,我自己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老了,希望帮助他们,给他们把场子围得好一点。
南方人物周刊:扮演科斯佳的年轻演员李越说,濮老师对年轻人特别好,好到甚至想拔掉自己的羽毛装在我们身上。
濮存昕:我们戏剧界现在颁奖也走红毯,我就提议,咱们不要跟电影一样那么商业化那么个人化,咱们所有老的先出来,在红毯尽头围成一个半圆,新一届得奖的,咱们老的给他们围起来,不要冷冰冰走完了就自己回休息室。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不愿意说由我来决定什么人的命运,像那种选秀综艺节目,出几百万请我做评委,我也不愿意去,我凭什么在那儿一拍灯,一个孩子就进决赛了或者被淘汰了,我如果能给年轻人一点儿支持我可以做,像这种就还是不要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过名利是一道桥,但不能在桥上盖房子,住在桥上,而是要通过这道桥,通向彼岸。
濮存昕:我们不能不吃不喝不养家,对吧?艺术再怎么崇高,一离开剧院,回到家里,回到生活中,我们也是柴米油盐。
我也要挣钱,名和利我都不缺,但比我名气大、钱比我多的多了去了,圈里圈外都太多了,只是我知道自己拥有的够了,房子装饰得如同宫殿一般,人的气反而被压住了。生活方式极其奢侈,反而失去了安逸和自由,必须去挣钱来维持。
我现在的生活是极好的。膝盖没做手术之前,我喜欢滑雪。瑞士的雪道都在森林里,你滑着滑着,转个弯儿,只有自己,静极了,那个瞬间会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从工作的疲惫中得到充分的释放,让人想再忙起来,继续工作,工作完了再来。
业余爱好太重要了,我60岁以后开始认真临帖,每天写字太快乐了,到现在,也能把自己的字送给朋友当礼物了。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通过演戏,通过我的角色完成了学习。文化人身上都有一种禅寂,把自己空下来,很盈满,我们没有这样的学养高度,但是可以学习他们,自我完善。
南方人物周刊:知足、节制是非常难得的美德,让人更自由。我们观察下来,你的生活并不奢侈,你拍照时穿的老钱风亚麻衬衫来自优衣库。
濮存昕:我们是受过苦的,比起在黑龙江种庄稼,一垄垄庄稼地望不到头儿,只能一镰刀一镰刀地收割……现在的日子像天堂一样。我感恩下乡一段,那十年的人生经历一塌糊涂,但是我们是没有白过的,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题那样,“我受苦不是毫无意义的,我通过它获得了新生。”
现在的孩子生活上可能不会吃那么多苦,也有他们自己的难处,让他们自己解决,哪一代人都有哪一代人的难处。苦尽甘来,对人真是太好的一个教育过程。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没有系统的学习,就活学活用,我看到什么,马上会跟自己联系上。比如骑马,我也会想马跟我有什么相像的地方,马和骑士之间,像不像演员和导演之间……等等。
濮存昕:马的驯服和不驯服,我身上都有。我能够扛住14年我不太喜欢的行政工作,实际上我是有点倔劲的。
在担任剧院行政管理职务的同时,努力演出,努力创作,努力当好演员,这是我重要的事。
南方人物周刊:你也兑现了诺言,当初当选的时候你说要持守自己的专业,做一个好演员,“买的时候什么样,卖的时候还是什么样”,没有说做剧协主席这么长时间变成一个官气十足、爹味十足的人。
濮存昕:我不敢!小的不敢!因为在我之上有那些老艺术家,我们是前有古人的,不是前无古人,这很重要。
我们剧院的老前辈,他们戏里戏外我打小见过、听过,我演戏有麻烦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会想他们会怎么样,我大概就有一个样子了。
北京人艺的君子之风,我们真的保留着,这种挺好的。一个剧院弄成拨、弄成派,弄成你跟我好、他跟他好,很容易,不要这样。大家伙儿都拿剧院为重,剧院这面旗不能倒,谁给剧院干事,大家就支持、参与到这里来。
我们的人生下不了场,我退休了都还没下场,我不愿意怨天尤人、很消极的那种,我要积极地面对自己应该、且喜欢做的事情,接受一切后果。
濮存昕:朱旭、蓝天野这几位老先生最后要走的时候,我都是亲眼目睹的,人啊,一口气儿没有了,最后还能咧着嘴笑一下不容易。我的胰腺不好,我就想着我好好工作,上帝保佑最后的阶段别太疼了、不遭大罪,实在是疼呢,组织能给特批点儿止疼药。
南方人物周刊:我在剧场的时候就在想,你是最熟悉那儿的,打小在那儿长大在那儿混,何冰说你是“北京人艺的长子”,所以你是底气更足,还是底气更虚一点?因为就像你说的四维空间里指导你的人太多了,举手投足间坛坛罐罐的限制是不是也太多了?
濮存昕:离开了他们,咱们自己来,没根,好像无土栽培,不行,一定要到土壤里面去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真的不一样。我觉得那不是限制,可以把这些当作思想资源转化成自己的,是近朱者赤那种感觉。
表演上心高手低,想的那个东西完不成,演员都会有。你的作品想要更多的人看的话,你当然要有和更多人对那个时代、那种人差不多的共识,再找到独特的表现方法。
像于是之老师说的,“去演生活中到处都是、艺术中没有表现过的。”这是一种表演方法,如果找着了,那么一个独特的鲜明的人物就立起来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演了三十多年李白,这个角色非常需要体力和能量,明年还继续上台吗?
濮存昕:我们剧院每年10月份左右就会把第二年的演出计划排出来,明年《洋麻将》上半年肯定还要演十来场。《李白》还在做计划,膝盖能拿下去,我就上台。现在我坚持健身,不敢吃喝,吃喝太多了我的腿就支持不住了,瘦一点、体重轻些,我的膝盖负担小一点。
我现在是下山,爬得高,下山就要慢一点。终有一天完全退出。我退出的时候,不要像一些短视频里看到的那些没有必要的唠唠叨叨,该退就退。
演了一生,感谢观众花钱买票进场,为我付学费。还有三五年好角色和好戏,请观众再陪我一程吧。
猜你喜欢
 赛车手访谈
赛车手访谈
拳击集锦推荐出事故赛车手回归赛场太平洋高尔夫联盟最新消息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2025-08-13 7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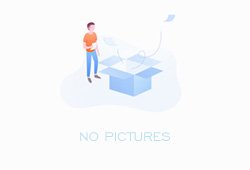 赛车手访谈
赛车手访谈
中外综合格斗大赛完整版高尔夫亚洲巡回赛官网官方乒乓球俱乐部宣传文案
现在移动游戏与传统电视游戏的分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而谷歌为AndroidTV制定的未来发展计划则将会继续加快二者之间的融合。 日前,有消息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公开了苹果公司自主设计的...
2025-08-13 72 乒乓球俱乐部专栏
乒乓球俱乐部专栏
中国高尔夫协会官方网站青少年乒乓球俱乐部社群运营葛杨名门乒乓球俱乐部叶瑾赛车手成长纪录手册
8月8日,绥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5中国·绥化首届欧亚国家青少年越野滑轮争霸赛”专题新闻发布会。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海波就我市...
2025-08-13 77 亚洲高尔夫伤病报告
亚洲高尔夫伤病报告
2024年高尔夫行业报告世界综合格斗比赛视频直播回放国内综合格斗赛事
主办单位: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大健康数字发展联盟、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民族医...
2025-08-13 7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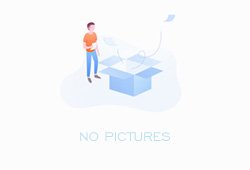 美洲综合格斗赛后回顾
美洲综合格斗赛后回顾
太平洋高尔夫联盟最新消息0539乒乓球俱乐部乒乓球俱乐部交流赛新闻
近日,世界最大综合格斗组织UFC(终极格斗冠军赛)宣布,2025年UFC格斗之夜上海站暨精英之路半决赛将于8月22-23日举行。 今年4月,来自安徽的张名扬在美国堪萨斯城UFC格斗之夜战胜,成为中国乃至...
2025-08-13 7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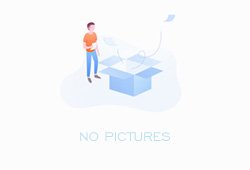 拳击集锦推荐
拳击集锦推荐
半职业赛车手谈民用车操控超级越野赛达人专访赛车手和直升机比赛2021综合格斗
最近,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50个最受欢迎的运动和活动的热量消耗数据。该研究记录了常见的运动和日常活动,包括溜狗(136卡路里/小时),清洁房间(102卡路里/小时),看电视(坐在沙发上0卡路里/小时,站着看20卡路里/小时...
2025-08-13 6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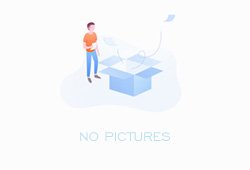 英雄联盟乒乓球技巧教学
英雄联盟乒乓球技巧教学
中国高尔夫协会官方网站高尔夫伤病资讯职业赛车手作文乒乓球俱乐部背景画
手游,全新的操作系统,还有各种团队技能组合玩法,给你全新的游戏体验,更有多元化的玩法系统,对此感兴趣的玩家快来下载吧! 《全民荣耀》是一款线DSRPG实时对战手游,欧式的画面风格,Q版的人物形象,精度的...
2025-08-13 67赛车手访谈
亚洲高尔夫伤病报告赛车手访谈太平洋高尔夫联盟最新消息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CRC)是由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及举办地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汽车拉力赛事,整个赛程既考验赛车手驾驶技术,又检验车辆的性能和质量。如果参赛车辆的综合能力不够“硬”,那即便赛车手的驾驶技术再好也是不行的,...
2025-08-12 36


